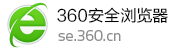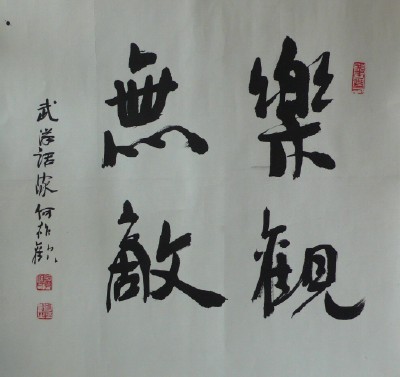
何祚欢,1941年3月生于武汉。国家一级演员,“中国评书、评话十大名家”之一,享受国务院终身津贴。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,湖北省文联副主席,湖北省曲协副主席,武汉市文联副主席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。武汉大学、华中科技大、华中师大等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或特约研究员。
长篇评书《杨柳寨》获全国优秀曲艺(南方片)观摩演出创作一等奖,短篇评书《挂牌成亲》获全国优秀曲艺作品一等奖。大型戏剧《穆桂英休夫》获1996年曹禺戏剧文学评奖提名奖,由创作小说改编的同名戏剧《养命的儿子》获文华奖、“五个一工程奖”。
今天初登上央视《百家讲坛》讲《水浒》。23日,何祚欢首次正式向媒体公布了这一消息,并揭秘了自己登上《百家讲坛》的来龙去脉。
何祚欢先生的首部文集——《何祚欢文集》 4月在新华诺富特饭店举行了隆重的首发仪式。
何祚欢先生的名人博客是http://blog.sina.com.cn/hezuohuan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幽默方言说书人
一个城市,拥有老百姓自发热爱的家喻户晓的艺术家,是一种幸福。就像北京拥有侯宝林,天津拥有马三立,铁岭拥有赵本山,武汉也拥有何祚欢。当然哪,我这么说的时候,可以想像何大哥会笑着摆手:“嘿嘿,人家是有全国影响,我只是武汉的‘土特产’。嘿嘿!”
得,何大哥,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“方便面时代”,扯一个歪瓜犟葫芦,恶煞煞地一炒,用开水一泡,就成了“全国影响”的什么“星”。但是,老百姓每到一个地方,要想带回家的,绝对是当地的土特产,而不是方便面。
说起何祚欢,就想到湖北评书。像天津快板、苏州评弹一样,湖北评书当然是属于湖北的。湖北评书源于宋代,在湖北武汉的土地上流传、发展,语言铿锵、韵律回旋,它独特的魅力、独特的幽默、独特的品位,为湖北和武汉的老百姓喜闻乐见。方言也许限制了它的“全国影响”,就像何祚欢到中央电视台去说书,也不得不改用普通话一样。但是,恰恰是因为方言的缘故,加上幽默的侃谈,何祚欢在武汉,整整半个世纪的岁月里,陶醉、征服了一代一代的听众观众,可以这么说,有的家庭三代人都是听何祚欢的评书长大的。上个世纪的60年代,他根据畅销全国的长篇小说《红岩》、《烈火金刚》等改编的《江姐上船》、《双枪老太婆》、《肖飞买药》等评书新段子,舞台上说,广播里播,风靡一时。那时候的中学生,摸错了一个,都会说几段何祚欢的评书,就像今天的孩子都会吼几句周杰伦的《双截棍》。
于是,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:和何大哥一起打的,的士司机一看是何大哥,硬是不肯收钱。他一出现在公共场所,就像吸铁石一样,大家兴奋地相告:“快来看啊,活的!活的‘活着欢’!”
才华横溢写书人
生长在汉正街的何祚欢,从小就喜欢评书。武汉一师毕业后,何祚欢到武汉四业中任教,后来又进入人才辈出的武汉说唱团,开始在曲艺界崭露头角。50年评书艺术风雨路,荣誉如珠,数得人眼花。
其实,何祚欢最厉害的本事,就是不但会说,而且会写。打着灯笼在全国找,能够自己写自己说的曲艺大师,真就没几个了。时至今日,湖北武汉的舞台上,电视晚会上,何祚欢的评书绝对是一个亮点。哪里有了他,哪里就有了笑声和欢乐。他创作的段子,紧贴现实,紧贴民间,紧贴老百姓的喜闻乐见、喜怒哀乐,像刚从地里摘下的黄瓜,鲜嫩嫩的,脆生生的,好爽口啊!说起武汉的历史掌故,文气充沛,如数家珍,好养人啊!将湖北评书,与武汉,与武汉人的性格,融为一体了,在武汉老百姓喜爱的品牌节目《都市茶座》中,他的评书已经到了“不似评书、胜似评书”的炉火纯青境界。
表演艺术上的名声太盛,以致掩盖了作为作家的何祚欢。这个多面手,不仅写评书,还写曲艺、写戏、写小说。他在担任武汉市文化局
创作中心主任期间,不仅带领创作团队创作了许多戏曲节目,自己还创作了京剧《穆桂英休夫》。他创作的“儿子系列”三部曲《养命的儿子》、《失踪的儿子》、《舍命的儿子》,既是耐读的系列长篇小说,又是他说书的最佳蓝本。
他的随笔,更是汪洋恣肆,妙趣横生。何大哥酷爱足球,有三届世界杯,他被报社秘藏于宾馆,深夜看完球,马上写评点随笔,一天一篇,十分过瘾。他的国学底子深厚,朋友雅集时,常常以古典诗词、对联相赠,才思敏捷,如同拈花微笑。他从艺50年来,著述达600多万字,最近,他与武汉出版社正式签约,凝聚其半生心血的《何祚欢文集》,精选评书、小说、散文、杂文、戏剧、自传、地方文史评述等各类作品约240万字,将于10月面世。
儒雅侠义平凡人
说书、写书,中年以后,何祚欢又迷上了书法。我和他在蔡甸纺织疗养院曾共住一楼潜心创作过。那时,他就每天早打太极,晚练书法。何家祚欢初爱家门何绍基,绍基乃晚清之大书家,其书法以颜为基础,参篆参隶,致力魏碑,乃得峻拔奇宕气势,自成一家。得了何家真气后,祚欢又拜湖北著名书法家陈义经为师,学其“金刚陈体”,师古而不泥古,藏巧于拙,似碑似帖,敦厚凝重,洒脱遒劲,时至今日,蔚然自成“何体”。走进他的工作室,好似走进书法展览厅,书香扑面,翰墨醉人。何祚欢的书法作品,常常写的是自己创作的诗词对联或者趣语,有时加上小款,十分爱人。现在的一些店铺,都以挂他的字为荣,那是聚集人气的吸铁石呢。
舞台上是艺术家,走下舞台,何祚欢便是洗尽铅华之平凡的真情汉子。“情浓处须放下酸文假醋,腹饥时且用些淡饭粗茶”,这是他自撰的一副对联,可视为其夫子自道。在朋友的眼中,他是儒雅饱学的文人,更是热情仗义,有侠士之风的大哥。他的工作室,常常成为武汉文艺界和朋友们雅集的“都市茶座”,管了香茶,还管酒饭。尤其是他煨的萝卜牛肉汤,那是相当的好喝。原武昌曲艺队的“湖北道情”曲种创始人之一周维,晚年生活清苦。何祚欢与周维素昧平生,却尽力相助,使他晚年生活有了保障。
大家看到的何祚欢,总是笑眯眯的,如善面菩萨,但面对不平,即刻就是怒目金刚。不义之人,千金难叫他开口;而我多次见到,会议期间,他专门到厨房,为普通的厨师说段子,让大家哈哈大笑。他常常说:“我叫何祚欢,就是‘活着欢’,活着就要给人带去欢乐。”这是何祚欢的座右铭,更是一个艺术家的大境界。
编辑手记 百变书生
何祚欢,我国评书艺坛上的一位“百变书生”,受棋道、迷中医、好书法、长烹调……5月9日,其个人文集出版签约,将于今年10月与读者见面,这也是国内首部曲艺家个人文集。几经预约,5月23日,记者走进何祚欢工作室,解读百变书生。
笑容可鞠的脸上,架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,这便是百姓喜爱的“活着欢”。他一边温壶泡茶,一边谈韵说诗。先生旷达而风趣,在武汉文艺界,流行不少有关他的笑话,最经典的取材他这双高度近视眼:武汉说唱团下乡,常走夜路,以策安全,领队号召几个女生为何先生引路。起初,女生们认真负责,一路沟沟坎坎总能领先生顺利跨过。久之,渐生懈怠,叽叽喳喳说得忘形,过一大沟,走出老远,才记起身后跟着的近视大哥。她们回头大声齐呼:“沟!”喊声方落,就听何先生闷声答道:“不必费心,我已经到沟里多时了!”
坊间笑谈不必考,有据为证的是,每每演出候场、出行候车时,何先生习惯挤时间看书,其状“织”如“嗅”。因为他拿着一本书在眼前来回穿梭,像织布;鼻子离书很近,如嗅味。“1983年,800度;1989年,1000度;近视眼的确以高速度与时俱进,最高到1500度。去年做了手术,还有300度。”且把眼镜去,咫尺不识君。
夫混沌初开,乾坤始奠。气之轻轻上浮者为天,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。天地之间,唯学能立人。诸子百家、民歌小调、俗词俚语、戏文杂书,读而迷,背而渊,今六十又五,何先生谈到兴处,诗赋文论脱口而出,情动于衷,手舞足蹈。想不到的是,他那背功源于“怕背打”。“读私塾时,背不出课文私塾先生要当堂打手心;没有体育用品,打架取乐就是私塾里的唯一体育远动。大点的学生打小学生,小学生打更小的学生,我这个4岁孩童,只能白送去给人打的。反抗无力,‘不许惹事’的家规又严,于是每日只有认真背读,以求早点回家。”
米兰·昆德拉说,“我们注定是扎根于前半生的一代人,即使后半生可能仍然充满了强烈的和令人感动的经历。”见流溯源,何先生前半生多精彩,少不得提其“说戏”蒙师———幺爹何昌万。“他让我坐在床上,自己拿了一条板凳,坐在我对面,正而八经地说开了《关公温酒斩华雄》:关羽请战被缚,几遭斩首,曹操说情松绑,赏酒壮行,关羽寄酒出战,战鼓喧天;帐中惊疑难定,关羽重回大帐,当众献上首级,杯中余酒尚温……”久泡书场自成师,《水浒传》、《三侠八俊十二雄》、《封神榜》等等,一部部从幺爹的肚子掏,继而一部部给同学们倒……
“杂食肚子”倒成了妙语仓库,俗不鄙,雅不玄。何先生由入道时讲《双枪老太婆》、《肖飞买药》等革命斗争故事的“红色宣传员”,变身为自撰自说《杨柳寨》、“儿子系列”三部曲(《养命的儿子》、《失踪的儿子》、《舍命的儿子》)等评书蓝本的“写书人”。厚积薄发,如今行文或全用赋体,或杂入骈句,日书6000字而不倦,像西西弗斯推动巨石上山那样,他是要在自己的作品中,安置无尽的山川、无言的日月和无边的丛林还有无滓的心灵。
办公地址:武汉市东西湖区七雄路
海峡创业城博士来大厦
24-25楼
武汉市武昌区秦园路东
原时光广场A座28楼
注册地址:武汉市东西湖区东西湖
大道5647号
电 话:027-82630119
027-88066119
传 真:027-83096700